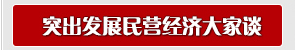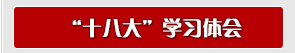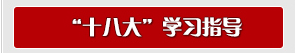我出生于1984年农历正月初九,属鼠的;按阳历算,是2月10日,水瓶座。在共和国的历史上,这一年有许多值得铭记的地方:邓小平首次视察深圳特区并题词、中国射击运动员许海峰在第二十三届洛杉矶奥运会上为中国夺得第一块金牌、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的国庆阅兵和群众游行活动,等等。当然,这一年发生的事,对于仍在襁褓中的我来说,都是未知的。
而今,我已34岁,虽然未用保温杯泡枸杞来养生,但毕竟不再是曾经的那个翩翩少年。借着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回眸一下我的成长、求学和工作经历,一方面可以坚定自己前行的脚步,另一方面,向祖国母亲汇报一下一个小镇青年在改革过程中受到的滋养,也不失为一种感恩。
成长:物质逐渐丰盈的90年代
我的籍贯是辽宁省昌图县,父母是地道的农民。1990年,在我6岁的时候,父母离开了土地所在地的农村,搬到了镇上,靠做一些小买卖生活。之所以搬到镇上,一方面是因为父亲所在的集体企业某某机修厂倒闭,另一方面母亲也想让我有一个更好的学习环境。
父亲学会了做豆腐的手艺,并日益精湛。他用卤水做出的豆腐,豆香浓郁、质地柔韧,深受好评。豆腐价格是0.2元/块,父亲每天做两盘豆腐,每盘有100块,全部卖掉的话,收入40元。扣除黄豆和其他成本,利润大概是15元。做豆腐既凭手艺,也很辛苦,父亲每天凌晨两点起床,将毛驴套上磨,开始做豆腐。凌晨五点,父亲赶着驴车出门,沿街叫卖热乎乎的豆腐。有时,白天还有别的零工要做,父亲就把做好的豆腐交给母亲去卖。印象中,童年唤我早起的,是父亲或母亲离开家门时那第一声悠长的吆喝:“豆——腐”。母亲更有经济头脑,她和几个相熟的朋友,去沈阳、鞍山进一些日用小百货,如小镜子、塑料梳子、纽扣等来卖,也是笔不小的收入。
1991年,我上小学了。那时,我最高兴的,是去邻居家看电视,看我根本无法理解的电视剧《上海的早晨》;后来我家也买了一台14寸的凯歌牌黑白电视机,《变形金刚》和《西游记》成了我的最爱;我最期待母亲去外地进货回来带的好吃的,0.8元一根的香肠,与今天最大的不同,就是肠体表面覆盖的那一层荤油,吃起来特别香;我也会羡慕小伙伴的变形金刚玩具,喜欢看彩色电视机里的《鼹鼠的故事》。暑假时候,我会去乡下爷爷家的稻田里玩,捉青蛙,或只是在夕阳下将双腿浸在漫灌的水里泡着;寒假时,我会央求父母买鞭炮,舍不得一下子点燃整个挂鞭,就拆散开来,一个一个的慢慢点燃。
1994年,我经历了人生中的第二次搬家。告别了15平的小土房,我们搬到了有60平的三间大瓦房。原来的房子卖了4400元,新居是16700元。新居是买的二手房,精心装修之后,焕然一新,成为很多亲戚、朋友羡慕的对象。这一年,父亲不再做豆腐了,他靠早年在机修厂积累的电焊手艺,在私人开的工场里打工;母亲不再卖百货,而是卖起了更有利润的服装。这一年,男孩们喜欢上了开封府的包青天和展昭,哼着“花花世界、鸳鸯蝴蝶”;女孩们迷上了杨钰莹,柔柔的唱着“让我轻轻的告诉你”;大人们则喜欢在夏夜聚在一起,用VCD唱着卡拉OK,一遍遍的重复着“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
1996年的夏天,我小学毕业。离别的伤感和对未知的憧憬,在小伙伴中间弥漫。空气中是老狼温暖的嗓音,“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最开心的人应该是文具店卖纪念册的老板娘,她进了无数种,也卖了无数种。
我在物质逐渐丰盈的90年代长大,不知不觉间体会着改革开放的甜头。
求学:扩招但升学竞争依然激烈00年代
小升初的那个暑假,母亲担心我无法适应初中新增的英语课程,花100元钱给我报了一个为期15天的英语班。那时候,小镇的英语教学水平不高,我学的也不认真,但这次补习令我受益良久:先是整个初中英语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后来在高中拿过两次全国竞赛的奖项,在大一时通过了英语六级考试。这样的成绩对于很小就开始英语启蒙的城里孩子来说,可能不算什么,但对小镇和农村的孩子来说,英语却是一道通往外部世界的闸门。我很庆幸,母亲帮我敲开了一道缝隙。
初中三年,是我逐渐懂事的三年,我越来越能理解父母的艰辛,也认识到了读书对于改变自己命运的重要性。同时,我也有幸遇到了一位正直善良、长于教学的班主任,他常常拿出自己的假期,免费给学生上课。数学专业毕业的他,讲起物理、化学游刃有余,也重视对我们综合素质的培养。1997年,学校为纪念香港回归举办了知识竞赛,我获得了一等奖,是一本新华字典;1998年,洪水肆虐南方,我和小伙伴们纷纷捐出了自己的零用钱;1999年,我不负众望,终于以小镇第二名的成绩考入了县城唯一一所重点高中。
由小镇而进入陌生的县城,开阔了我的眼界,住校生活让我更早的去适应在群体生存的规则。尤记得1999年冬天,假期未离校的同学一起观看了澳门回归祖国的现场直播;尤记得2001年7月,大家在下了晚自习后,聚拢在收音机前,密切关注着北京申奥的一举一动,直到国际奥委会做出将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交给北京后,宿舍楼里一片欢呼雀跃,整个校园和县城都沸腾起来。
自1999年开始实行的高考扩招,让更多的人圆了大学梦,我却在2002年的高考中因发挥失常而落榜。复读一年后,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到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2003年8月到校报到,是小镇出身的我第一次到首都北京,那种激动和愉悦,至今难忘。
大学四年是自由读书的四年,我也参与了白鸽青年志愿者协会等公益组织;毕业前夕,我获得了保研资格。出于对互联网的期待,我选择了以通信和计算机闻名的北京邮电大学去读新媒体与网络传播的研究生。
工作: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汽车行业,值得我们为之奋斗
2010年硕士毕业后,我回到吉林、进入一汽工作。先是在整车销售公司做了三年多的市场工作,包括乘用车的广告投放和公关活动的执行;2014年,我转向了更具挑战的销售领域,工作至今。
一汽是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从1953年7月一汽奠基,到1956年7月“解放牌”载货汽车下线,结束了中国不能制造汽车的历史。1958年,一汽又诞生了“东风牌”小轿车和红旗牌高级轿车。自此,红旗成为国家礼宾用车和国家领导人乘坐的庆典检阅车。自90年代以来,以一汽大众为代表的合资车企,更是中国汽车行业的领头羊。一汽的历史和发展是值得骄傲的,这份骄傲也激励每个一汽人砥砺前行。
时至今日,中国已成为产销超过2000万辆的汽车市场,自主品牌车企日渐崛起,合资品牌群雄逐鹿,同时,越来越多的新兴车企投入到新能源和智能化汽车制造,使得竞争异常激烈。今年以来,国家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降低了制造业增值税、整车和零部件进口关税,并逐渐放开汽车企业合资股比,可以预期的是,中国汽车行业的未来注定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亲历行业变革的高潮,是从业者的幸事;拥抱并享受它,需要我们拼尽全力。
结语
作为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孩子,我对自己身份的定位是80后“小镇青年”,为的是铭记父母和师长的教育之恩;作为一个在百年名校受过熏陶的大学生和九三学社社员,我以一个准知识分子的身份要求自己去关注和分析这个世界;作为一个汽车行业的从业者和一汽的一份子,我会站在企业未来发展的高度去看待自己的工作,努力将最好的服务提供给客户。
改革开放四十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种成果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是纸上的数字,更是脸上的笑容和灵魂的满足。感谢英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引导中国人民独立、自强,让我们身为中国人而自豪! |